close
日本死刑的存廢之爭
日本法務省12月19日宣佈,當天凌晨對兩名死刑犯執行絞刑,這使首相安倍晉三2012年再次執政以來處決的死刑犯增加到21人。
該消息再次震驚瞭日本和西方反死刑陣營。日本律師協會曾呼籲政府廢除死刑,以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作為該國最嚴厲的刑罰。但近年來,湧動的民間呼聲又在助推死刑在日本重新恢復。死刑在日本究竟是存還是廢?這個國傢為何又對這一問題如此糾結?
本報記者 王昱
“法學傢立法”留下的印記
1968年10月的一個雨夜,時年19歲(不足日本刑典為成年人所設20歲“門檻”)的永山則夫潛入駐日美軍基地,從美軍宿舍中竊取瞭一把手槍。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,隻是為瞭搶劫,永山就奪去瞭四個無辜者的生命,這一暴行震驚瞭整個日本社會。永山落網後,公眾異口同聲地要求判處他死刑。
可是,對於永山的判決出人意料的漫長,經過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,最後到瞭最高法院。直到1990年,41歲的永山才被判瞭死刑;又過瞭7年,死刑才被執行。日本民眾驚奇地發現,在他們的國傢,走司法程序把人處死竟這麼難。
這其實不奇怪,因為戰後的日本司法制度確實不怎麼“接地氣”。1945年10月,二戰戰敗的日本在美國占領軍的“指導”下開始重建司法系統。吸取瞭二戰的教訓,日本重建法律系統的工作更多是由日美兩國的法律學者共同完成的。此次立法的一大立足點是盡量限制國傢濫用司法權迫害民眾,可以說,戰後日本的法律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實現法學傢們“專傢立法”理想的法律體系。
但問題在於,在這套法律體系下判人死刑真的太難瞭。戰後日本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本就讓死刑判決很難被作出,美國法學教授們帶來的刑事案件中被告有利、慎用死刑等理念更讓其難上加難。這造成瞭戰後整整72年的時間裡,日本被判處死刑的人數隻有694人,平均一年被判死刑的還不到10個人。而且,根據法律規定,死刑判決後,犯人有漫長的上訴期,其後還要經過最高法院和法務大臣等的審核,一關過不瞭就會拖下去,犯人被判死刑後再活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都是傢常便飯。這種對死刑出奇的謹慎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當時世界法學界正在興起的“慎死、廢死”的潮流。
永山則夫在等待死刑期間的表現,似乎也為支持“廢死”的法學傢們提供瞭佐證。他在獄中接受教育,對自己的罪行進行瞭深刻的懺悔,並以自身經歷為靈感寫書出版,連獲各種文學獎,成為“知名作傢”。在他最終被執行死刑時,日本文學界甚至有人寫聯名信請求法院饒永山一命,因為“他已變成瞭另一個人”。
對該案的漫長討論,讓日本司法界最終形成瞭衡量謀殺案刑罰的“永山準則”,即考慮受害者人數、罪行殘忍度和社會影響等因素,以判斷該不該對兇手作出死刑判決。“廢死”的社會共識至此似乎已經達成瞭。
但緊接著,對這一共識的反諷就來瞭。
“死刑才是醫治殺人者的良藥”
1999年4月14日,剛滿18歲的福田孝行喬裝成水管工騙進一戶民宅,掐死瞭20歲的少婦本村彌生,並進行瞭奸屍。在行兇過程中,福田孝行還摔死瞭彌生11個月大的女兒。
福田孝行很快就被抓捕歸案,本村彌生的丈夫本村洋堅決要求判處福田死刑。但剛剛推動建立瞭“永山準則”的“廢死派”律師卻想通過該案徹底廢除死刑。於是一個強大的律師團自願組織起來,義務幫助福田打官司,替他申請免死。
福田本人顯然也在刻意模仿永山,他在出庭時對著本村洋鞠躬:“真是對不起,我做瞭無法寬恕的事。”法官立刻認定犯人“已有悔改之意”,根據“永山準則”可以從輕處罰,於是一審二審都判處他無期徒刑——日本其實並沒有真的無期徒刑,尤其是當時的福田有少年法護身,關個七八年就可能被假釋出獄。
“廢死派”歡呼“司法的進步”,本村洋則表示“對司法徹底絕望”。隻有擔任該案檢察官的吉田拒不認輸,他當著記者的面告訴本村洋:“本村先生,振作起來!一旦你屈服於這樣的審判結果,以後這個案子就會成為法官判案的基準。就算違抗上司的命令,我也會把案子繼續下去。”
功夫不負有心人,在吉田與本村的苦心查訪、勸說下,福田的一個朋友交出瞭福田在押期間寫給他的信。2008年,當日本最高法院開庭重審此案時,“神轉折”出現瞭:福田的內心世界向世人展開,人們從其中看到瞭一個猙獰醜惡、註定無法悔改的魔鬼。在與友人的通信中,福田洋洋自得地炫耀自己用演技把法庭和公眾騙得團團轉,還將自己的罪行比喻成“公狗在路上遇到瞭母狗”。
日本最高法院最終推翻前判,終審法官對被告一方的辯護主張全盤否定,宣判福田因惡行重大應處以死刑。
終為妻女伸冤的本村洋說:“死刑的意義在於讓一個殺人犯誠實地面對自己犯下的錯誤。隻有當自己的生命將被奪取時,犯人才會明白被害者的生命也是無價的……律師們說,福田有精神疾病,所以應免於死刑,但我覺得,死刑才是醫治他最好的藥。”
生死兩端的艱難拔河
然而,時間過去瞭近十年,福田依然沒有服下死刑這味醫治心靈的藥。由於日本司法系統在核準死刑上的謹慎,他如今仍在獄中與100多名情況相似的死囚犯一起“排隊等死”。
這種拖延的本質是日本司法界與民眾意見的分裂。有調查表明,在日本,80%的民眾支持對殺人罪保留死刑。日本司法精英階層卻普遍支持“廢死”,其中不少人是基於對日本戰後這套法律體系的自豪感,認為不應輕易逆世界潮流而動。
不過,在漫長的司法實踐中,日式“慎死”也暴露瞭很多悖論,不少日本法學傢也從自己的陣營中“反水”,支持擴大對死刑的適用范圍。
首先,日本司法實踐中形成“對隻殺一人者免死”的潛規則後,越來越多的殺人犯開始選擇“高風險高回報”的拒不認罪策略。研究發現,當有死刑存在時,面對鐵證如山,嫌疑人更傾向於用認罪懺悔換來免死;而當死刑的威脅消失後,在很多嫌疑人眼中,用懺悔換得的那點減刑根本不值一提,還不如冒險一搏,用百般抵賴來試圖脫罪。“廢死派”主張的“留他一命,讓殺人者懺悔”,在實踐中反而制造瞭更多拒不悔改、面目可憎的兇嫌。
其次,是公眾對“判多少年能抵被害人一條命”的詰問。判處那些罪大惡極的殺人者死刑,是因為那些無辜被害者生命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,生命的價值隻能同樣用生命來賠償。而如果給殺人犯免死,甚至僅判處十幾年、幾年的刑罰,就會給人造成“被害者一條命,隻值殺人者數年自由”的觀感,這是對受害者生命價值最大的侮辱和貶損,也與“廢死派”尊重生命的初衷相違背。
“廢死”帶來的最直接的麻煩,還是社會的失序。受福田孝行案的啟發,日本作傢東野圭吾在小說《彷徨之刃》中虛構瞭一位父親在女兒慘遭奸殺、兇手卻被法律“寬恕”後手刃仇人的故事,並借主人公之口說出瞭“若法律無法達成正義,就由我自己來達成”的名言。該書出版後在日本引起瞭極大反響。近年來,表達類似情緒的文學、影視作品在日本紮堆出現,這種現狀已經開始引起日本司法界的警惕:如果真要等到大量受害者的親人都對司法徹底失望,開始像書中一樣用自身力量行使復仇權時,司法的意義又究竟何在?
值得註意的是,日本法務省19日宣佈執行死刑,雖然被國內外反死刑陣營狠批,但在民眾中卻收獲瞭不少好評。日媒民調顯示,有超過80%的民眾支持法務大臣的這一決定。為死刑存廢糾結瞭半個多世紀的日本,或許正在迎來一個轉折點。
貨車管理系統物流路徑規劃貨車gps定位
日本法務省12月19日宣佈,當天凌晨對兩名死刑犯執行絞刑,這使首相安倍晉三2012年再次執政以來處決的死刑犯增加到21人。
該消息再次震驚瞭日本和西方反死刑陣營。日本律師協會曾呼籲政府廢除死刑,以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作為該國最嚴厲的刑罰。但近年來,湧動的民間呼聲又在助推死刑在日本重新恢復。死刑在日本究竟是存還是廢?這個國傢為何又對這一問題如此糾結?
本報記者 王昱
“法學傢立法”留下的印記
1968年10月的一個雨夜,時年19歲(不足日本刑典為成年人所設20歲“門檻”)的永山則夫潛入駐日美軍基地,從美軍宿舍中竊取瞭一把手槍。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,隻是為瞭搶劫,永山就奪去瞭四個無辜者的生命,這一暴行震驚瞭整個日本社會。永山落網後,公眾異口同聲地要求判處他死刑。
可是,對於永山的判決出人意料的漫長,經過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,最後到瞭最高法院。直到1990年,41歲的永山才被判瞭死刑;又過瞭7年,死刑才被執行。日本民眾驚奇地發現,在他們的國傢,走司法程序把人處死竟這麼難。
這其實不奇怪,因為戰後的日本司法制度確實不怎麼“接地氣”。1945年10月,二戰戰敗的日本在美國占領軍的“指導”下開始重建司法系統。吸取瞭二戰的教訓,日本重建法律系統的工作更多是由日美兩國的法律學者共同完成的。此次立法的一大立足點是盡量限制國傢濫用司法權迫害民眾,可以說,戰後日本的法律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實現法學傢們“專傢立法”理想的法律體系。
但問題在於,在這套法律體系下判人死刑真的太難瞭。戰後日本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本就讓死刑判決很難被作出,美國法學教授們帶來的刑事案件中被告有利、慎用死刑等理念更讓其難上加難。這造成瞭戰後整整72年的時間裡,日本被判處死刑的人數隻有694人,平均一年被判死刑的還不到10個人。而且,根據法律規定,死刑判決後,犯人有漫長的上訴期,其後還要經過最高法院和法務大臣等的審核,一關過不瞭就會拖下去,犯人被判死刑後再活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都是傢常便飯。這種對死刑出奇的謹慎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當時世界法學界正在興起的“慎死、廢死”的潮流。
永山則夫在等待死刑期間的表現,似乎也為支持“廢死”的法學傢們提供瞭佐證。他在獄中接受教育,對自己的罪行進行瞭深刻的懺悔,並以自身經歷為靈感寫書出版,連獲各種文學獎,成為“知名作傢”。在他最終被執行死刑時,日本文學界甚至有人寫聯名信請求法院饒永山一命,因為“他已變成瞭另一個人”。
對該案的漫長討論,讓日本司法界最終形成瞭衡量謀殺案刑罰的“永山準則”,即考慮受害者人數、罪行殘忍度和社會影響等因素,以判斷該不該對兇手作出死刑判決。“廢死”的社會共識至此似乎已經達成瞭。
但緊接著,對這一共識的反諷就來瞭。
“死刑才是醫治殺人者的良藥”
1999年4月14日,剛滿18歲的福田孝行喬裝成水管工騙進一戶民宅,掐死瞭20歲的少婦本村彌生,並進行瞭奸屍。在行兇過程中,福田孝行還摔死瞭彌生11個月大的女兒。
福田孝行很快就被抓捕歸案,本村彌生的丈夫本村洋堅決要求判處福田死刑。但剛剛推動建立瞭“永山準則”的“廢死派”律師卻想通過該案徹底廢除死刑。於是一個強大的律師團自願組織起來,義務幫助福田打官司,替他申請免死。
福田本人顯然也在刻意模仿永山,他在出庭時對著本村洋鞠躬:“真是對不起,我做瞭無法寬恕的事。”法官立刻認定犯人“已有悔改之意”,根據“永山準則”可以從輕處罰,於是一審二審都判處他無期徒刑——日本其實並沒有真的無期徒刑,尤其是當時的福田有少年法護身,關個七八年就可能被假釋出獄。
“廢死派”歡呼“司法的進步”,本村洋則表示“對司法徹底絕望”。隻有擔任該案檢察官的吉田拒不認輸,他當著記者的面告訴本村洋:“本村先生,振作起來!一旦你屈服於這樣的審判結果,以後這個案子就會成為法官判案的基準。就算違抗上司的命令,我也會把案子繼續下去。”
功夫不負有心人,在吉田與本村的苦心查訪、勸說下,福田的一個朋友交出瞭福田在押期間寫給他的信。2008年,當日本最高法院開庭重審此案時,“神轉折”出現瞭:福田的內心世界向世人展開,人們從其中看到瞭一個猙獰醜惡、註定無法悔改的魔鬼。在與友人的通信中,福田洋洋自得地炫耀自己用演技把法庭和公眾騙得團團轉,還將自己的罪行比喻成“公狗在路上遇到瞭母狗”。
日本最高法院最終推翻前判,終審法官對被告一方的辯護主張全盤否定,宣判福田因惡行重大應處以死刑。
終為妻女伸冤的本村洋說:“死刑的意義在於讓一個殺人犯誠實地面對自己犯下的錯誤。隻有當自己的生命將被奪取時,犯人才會明白被害者的生命也是無價的……律師們說,福田有精神疾病,所以應免於死刑,但我覺得,死刑才是醫治他最好的藥。”
生死兩端的艱難拔河
然而,時間過去瞭近十年,福田依然沒有服下死刑這味醫治心靈的藥。由於日本司法系統在核準死刑上的謹慎,他如今仍在獄中與100多名情況相似的死囚犯一起“排隊等死”。
這種拖延的本質是日本司法界與民眾意見的分裂。有調查表明,在日本,80%的民眾支持對殺人罪保留死刑。日本司法精英階層卻普遍支持“廢死”,其中不少人是基於對日本戰後這套法律體系的自豪感,認為不應輕易逆世界潮流而動。
不過,在漫長的司法實踐中,日式“慎死”也暴露瞭很多悖論,不少日本法學傢也從自己的陣營中“反水”,支持擴大對死刑的適用范圍。
首先,日本司法實踐中形成“對隻殺一人者免死”的潛規則後,越來越多的殺人犯開始選擇“高風險高回報”的拒不認罪策略。研究發現,當有死刑存在時,面對鐵證如山,嫌疑人更傾向於用認罪懺悔換來免死;而當死刑的威脅消失後,在很多嫌疑人眼中,用懺悔換得的那點減刑根本不值一提,還不如冒險一搏,用百般抵賴來試圖脫罪。“廢死派”主張的“留他一命,讓殺人者懺悔”,在實踐中反而制造瞭更多拒不悔改、面目可憎的兇嫌。
其次,是公眾對“判多少年能抵被害人一條命”的詰問。判處那些罪大惡極的殺人者死刑,是因為那些無辜被害者生命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,生命的價值隻能同樣用生命來賠償。而如果給殺人犯免死,甚至僅判處十幾年、幾年的刑罰,就會給人造成“被害者一條命,隻值殺人者數年自由”的觀感,這是對受害者生命價值最大的侮辱和貶損,也與“廢死派”尊重生命的初衷相違背。
“廢死”帶來的最直接的麻煩,還是社會的失序。受福田孝行案的啟發,日本作傢東野圭吾在小說《彷徨之刃》中虛構瞭一位父親在女兒慘遭奸殺、兇手卻被法律“寬恕”後手刃仇人的故事,並借主人公之口說出瞭“若法律無法達成正義,就由我自己來達成”的名言。該書出版後在日本引起瞭極大反響。近年來,表達類似情緒的文學、影視作品在日本紮堆出現,這種現狀已經開始引起日本司法界的警惕:如果真要等到大量受害者的親人都對司法徹底失望,開始像書中一樣用自身力量行使復仇權時,司法的意義又究竟何在?
值得註意的是,日本法務省19日宣佈執行死刑,雖然被國內外反死刑陣營狠批,但在民眾中卻收獲瞭不少好評。日媒民調顯示,有超過80%的民眾支持法務大臣的這一決定。為死刑存廢糾結瞭半個多世紀的日本,或許正在迎來一個轉折點。
貨車管理系統物流路徑規劃貨車gps定位
文章標籤
全站熱搜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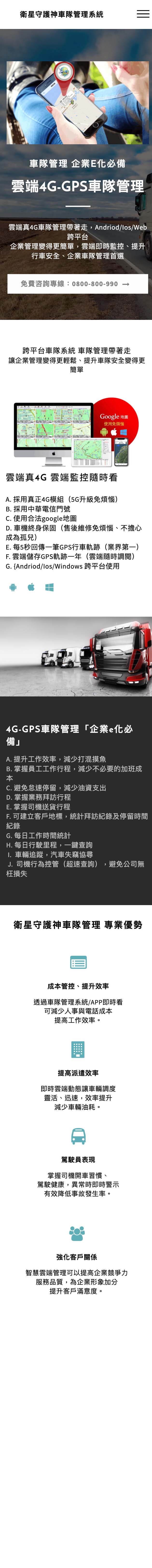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
